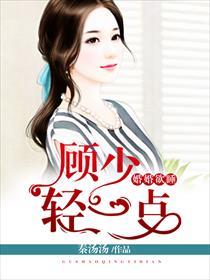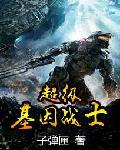笔趣阁>华夏真相集 > 第五十八集 韦武合谋(第3页)
第五十八集 韦武合谋(第3页)
中宗见众议汹汹,已成千夫所指之势,万不得已,只得下诏,命流配郑普思于海南儋州;尽搜其雍、岐二州余党,皆令诛之。
又说安乐公主,因得李显尤为溺爱,便自恃宠骄恣,卖官鬻狱,势倾朝野。或自为制敕诏令,呈于父皇用印时却以手掩其文字内容,强令皇帝签署。
中宗每皆笑而从之,挥笔签字,竟不视其内文。
时因皇太子李重俊不是韦后亲生,安乐公主自以为皇后嫡出,竟自奏请为皇太女,盖欲使父皇废黜太子,以己自代为嗣。
中宗以此事询问宰相,魏元忠奏道:皇太子乃国之储君,生民之本。今既无罪,岂得动摇?况若以公主为皇太女,来日驸马将用何名号?天下必甚惊怪,恐非公主自安之道。
中宗于是不从公主所请,然亦不加遣责。
神龙二年,禅宗六代首座弟子神秀法师圆寂。
镜头闪回,补叙神秀来历平生。
神秀俗家姓李,开封尉氏人,早年学习经史,其后出家为僧。五十岁时,才到蕲州双峰山东山寺(湖北黄梅县东北),谒见禅宗五祖弘忍求法,从事打柴汲水等杂役六年。
弘忍对神秀深为器重,称其为悬解圆照第一,令为众僧教授师。及至晚年,弘忍算出自己将要圆寂,为传付达摩祖师衣钵法门,便命阖寺弟子,各作一偈以呈。
神秀作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当时惠能在寺中为杂役,尚未落发为僧,且不识字,便口诵一谒,请人书之于白墙。弘忍路过,观其谒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五祖大喜,遂暗传衣钵与惠能。
五祖弘忍死后,神秀在江陵当阳山玉泉寺大开禅法,声名远播,四海僧俗闻风而至。
武皇则天闻其盛名,深相敬重,命于当阳山置度门寺,更在神秀家乡尉氏建报恩寺,以旌其德。久视元年,遣使迎至洛阳,后到长安内道场,时年神秀法师已九十余岁。
中宗及睿宗在位期间,更加礼重,因此被世人尊为“两京法主,三帝国师”。据说中书令张说也向神秀问法,并执弟子之礼。
闪回结束。神龙二年,神秀法师在洛阳天宫寺圆寂,寿止于一百单二岁。
唐中宗赐以“大通禅师”谥号,并根据神秀遗愿,下诏归葬当阳度门寺,赐钱敕建砖石塔。左丞相燕国公张说为其撰写碑文,极具哀荣。
神秀弟子普寂、义福继续阐扬其宗,盛极一时。
其后惠能弟子神会论定南北两宗,以神秀之禅由方便入为渐门,以惠能之禅直指人心为顿门,于是便有南顿北渐之分。
然而北宗禅仅传数代即衰,后由普寂弟子道璇将其传往日本。
唐神龙二年十二月,突厥默啜可汗引兵来攻鸣沙(黄河青铜峡南)。中宗李显派灵武军大总管沙吒忠义为帅,率兵与战。力战之下,唐军遭受前所未有大败,损折六万余人。
突厥遂乘胜驰掠原州、会州,得马万余匹而去。中宗大怒,命将沙吒忠义免官为民。更命内外诸官,各进平定突厥之策。
右补阙卢俌上疏:昔有郤谷悦礼乐,敦诗书,为晋国元帅;杜预射不穿礼,故建平吴之勋。是知中权制谋,不取一夫之勇。如沙吒忠义者,仅为骁将之材,本不足以当元戎大任。又鸣沙之役,主将先逃,宜正邦宪;赏罚既明,敌无不服。又边州刺史,宜精择其人,使之蒐卒乘,积资粮,来则御史,去则备之。去岁四方旱灾,未易兴师。当理内以及外,绥近以来远,俟仓廪实,士卒练,然后大举以讨之。
中宗览疏称善,于是便令诸宰举荐良将,并实仓廪,以备再次征伐。
神龙三年,春三月庚子。吐蕃赞普弃隶蹜赞祖母遣大臣悉薰热入贡,并求赐公主为婚。唐中宗从之,以自己所养雍王李守礼之女金城公主,许嫁吐蕃赞普。
五月戊戌,以右屯卫大将军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来犯。只因岁旱谷贵,便召太府卿纪处讷入内与谋。纪处纳刚娶武三思姨妹为妻,是为连襟姻亲。
明日早朝,武三思便唆使知太史事迦叶志忠进奏:臣夜观天象,见摄提入于太微宫,直至帝座,乃主大臣宴见,纳忠谏于天子之兆也。
中宗回忆昨夜召见情况,赞道:未料纪卿之忠诚,竟上彻于天象!
遂命赐纪处讷锦衣一袭,绢帛六十段。
韦皇后以太子李重俊非己所生,由此深为厌恶,便与武三思同谋,欲将太子设计罢黜。昭容上官婉儿亦参与其中,每于草拟制敕时推尊武氏,上下其手。
安乐公主与驸马左卫将军武崇训更常陵侮太子,当面呼为贱奴。更兼武崇训又教公主请废太子,李重俊故此积恨,便与宰相魏元忠密议。
魏元忠献计:殿下欲图除灭武三思家族,则非拉拢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为同党不可。
太子问道:却是为何?
魏元忠答道:李多祚世为靺鞨酋长,率部归顺唐朝,骁勇善战,先后参与平定后突厥、黑水靺鞨、室韦及契丹反叛。因屡立军功,累迁右羽林军大将军、上柱国、辽阳郡王,掌握禁兵、宿卫北门二十余年。又为神龙功臣,亦得天子信赖。以其为助,事无不成。
太子李重俊信以为然,遂密召李多祚入宫,说与己愿。
李多祚深恨武三思,于是欣然同意,遂与兵部尚书魏元忠议定起事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