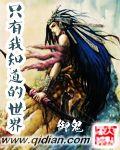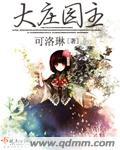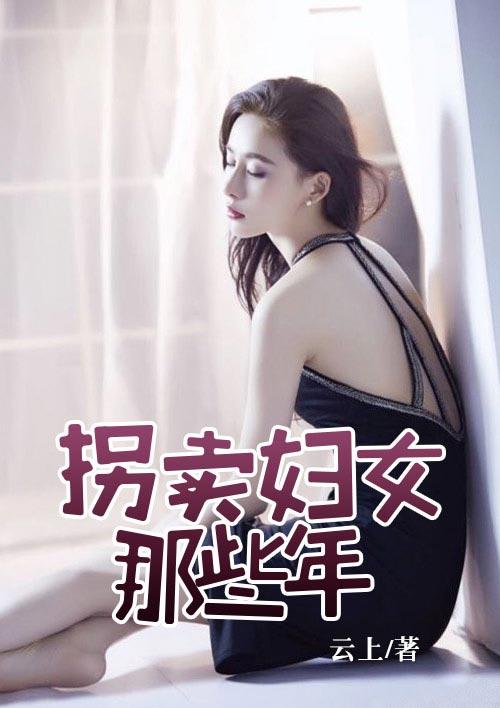笔趣阁>云麓词心录:白云着 > 第305章 四君子笺(第2页)
第305章 四君子笺(第2页)
煜明坐在竹屋前的石凳上,手中握着刚写完的《咏竹》诗稿,墨香混着竹叶的清气,格外提神。院中那丛湘妃竹被雨水洗得发亮,竹节上的斑点如泪,正如诗中所写“翠影摇风逸韵长,霜凌雨蚀志轩昂”。
“好个‘虚怀若谷青云意,劲节凌云浩气扬’!”子衡推门进来,肩头还带着雨珠,手里提着个竹编的鱼篓,“方才在溪边钓鱼,见这雨下得酣畅,便想着你定在写竹,果然没猜错。”
煜明起身接过鱼篓,里面有几条活蹦乱跳的石斑鱼:“你来得正好,刚写完这首诗,正想听听你的见解。你看这‘常伴幽林吟雅颂,耻栖俗苑逐炎凉’,可写出了竹的风骨?”
子衡将鱼篓放在檐下,拿起诗稿细看,雨打在竹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为诗伴奏。他读了几遍,忽然指着“七贤逸兴今何在,林畔犹闻啸咏章”笑道:“这两句用竹林七贤的典故,倒是妙极。你是想说,如今虽无阮籍嵇康,你我却可在这云麓山,做个竹下的隐士?”
煜明点头,递过一杯新泡的竹叶茶:“昨夜雨歇时,我在竹林里散步,见新笋破土,老竹挺拔,忽然就想起七贤的故事。你说当年嵇康在竹林里打铁,是否也像我们这样,听着竹风,喝着竹茶,不问世事?”
茶烟袅袅,子衡望着院中摇曳的竹影,想起五年前,他们刚到云麓山时,亲手种下这片竹林。那时煜明说:“竹有三德,中空似虚心,有节似守节,挺拔似正直,此乃君子之象。”如今竹林成荫,他们的友情也如这竹子般,在岁月里节节拔高。
“记得你第一次为竹写诗,”子衡放下茶杯,指尖划过石桌上的竹纹,“还是用隶书写的,字里行间都是刚劲。后来你说,竹最难得的是‘未出土时便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这与你我追求的境界,倒是不谋而合。”
雨渐渐小了,阳光透过竹叶的缝隙洒在石桌上,形成斑驳的光影。煜明想起在京城时,子衡曾因不肯附和权贵而被排挤,那时他送了子衡一幅墨竹图,题字“任尔东西南北风”。如今看来,他们终究是如竹子般,守住了心中的气节。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你这诗里,我最喜欢‘霜凌雨蚀志轩昂’一句,”子衡忽然开口,目光落在雨中的竹林,“你看这竹子,无论风霜雨雪,总是挺直了腰杆。就像我们这些年,虽远离仕途,却在这云麓山活出了自己的样子,这不正是‘劲节凌云浩气扬’吗?”
煜明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只见竹林在风中轻轻摇曳,却从未弯曲。他想起诗中的“虚怀若谷”,忽然觉得,人若能像竹一样,既有挺拔的气节,又有谦逊的胸怀,便是最好的状态。
“说起来,”子衡起身走到竹林边,伸手接住一片飘落的竹叶,“我们该给这竹林起个名字。当年七贤有‘竹林’,我们这云麓山的竹林,也该有个雅号。”
煜明沉吟片刻,望着连绵的竹影:“不如叫‘逸韵林’?取你诗中‘翠影摇风逸韵长’之意,也暗合我们追求的逸致。”
“好!”子衡抚掌笑道,“‘逸韵林’,好名字!待日后我们编一部《云麓竹谱》,就以此为名。”
两人说笑着,开始准备午饭。煜明杀鱼,子衡生火,厨房里飘出阵阵香气。窗外的竹林在雨后更显青翠,竹影摇风,仿佛在吟唱着一首关于气节与友情的诗。
当夕阳透过竹梢洒下金辉时,两人坐在“逸韵林”中,桌上摆着刚出锅的笋烧鱼,还有一坛自酿的竹露酒。煜明举杯道:“敬这云麓山的竹,也敬你我如竹般的友情,历经风雨,始终如一。”
子衡举杯相碰,酒液清冽,一如这竹林的清气。他看着煜明眼中的光,忽然觉得,这世间最难得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能与知己在竹影摇风处,喝一杯竹酒,吟一首竹诗,守着一份如竹般挺拔而虚心的情谊。
第四章菊艳东篱下
云麓山的秋意,是从东篱的菊蕊开始的。
煜明蹲在菊圃前,为一株墨菊系上竹架。花瓣墨紫如缎,在夕阳下泛着微光,正如诗中所写“霜风凄紧绽金黄,冷露含馨傲冷霜”。他身后的竹篱上爬满了各色菊花,黄的如金,白的似雪,开得轰轰烈烈。
“你这‘不贪春景繁花艳,独守秋篱晚节彰’,”子衡提着一壶菊花酒走来,酒香中混着菊香,“倒是把菊花的性子写透了。我今早去镇上打酒,听见茶肆里有人念你的诗,说‘陶令篱边诗意涌,东篱把盏醉斜阳’,倒像是看见了你我赏菊的模样。”
煜明直起身,接过酒壶擦了擦手:“今早起来,见菊圃里的‘醉西施’开了,那花瓣卷卷的,像美人醉酒,忽然就想起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你说当年陶令若是见了我这菊圃,会不会多喝几杯?”
子衡将酒壶放在石桌上,取出两个陶杯:“依我看,陶令见了定会喜欢。你这菊圃里种了三十多种菊,从‘墨麒麟’到‘玉壶春’,哪一株不是风骨独具?就像你诗里说的‘逸韵盈枝凝素志,幽姿照野散清香’,连香气都带着清傲。”
夕阳将菊圃染成金色,花瓣上的露珠折射出七彩的光。煜明想起三年前,子衡从山下带回一包菊种,两人一起翻土、施肥、育苗,如今菊圃已成规模,每到秋天,便是云麓山最美的风景。
“记得你第一次种菊,”煜明斟满酒杯,看着杯中浮动的菊花瓣,“把‘绿牡丹’错当成野草拔了,气得你三天没理我。后来才知道,那绿菊初开时,叶片确实像野草。”
子衡闻言大笑,脸上泛起红晕:“别提了,那时不懂菊性,闹了不少笑话。后来读了《菊谱》才知道,菊花品种繁多,各有性情,就像人一样,不可貌相。”
酒过三巡,两人沿着菊篱散步。子衡忽然指着一株开得最盛的黄菊:“你看这‘金背大红’,背面金黄,正面深红,开得如此热烈,却又在秋霜中傲然挺立,倒像是你诗里‘冷露含馨傲冷霜’的写照。”
煜明停下脚步,望着暮色中的菊圃,想起在京城时,他们曾在重阳日去登高赏菊,那时人人都爱谈论仕途,唯有他们对着菊花,背诵陶渊明的诗。如今想来,那时的心境,早已预示了今日的归隐。
“你这诗的结句用陶令的典故,”子衡忽然开口,目光落在远方的山峦,“可是有感而发?我知道你心里,始终敬佩陶令的洒脱。”
煜明点点头,摘下一朵雏菊别在子衡的衣襟上:“是啊,‘东篱把盏醉斜阳’,多么自在的境界。有时我想,我们在这云麓山种菊、赏菊、写菊,不就是在追寻陶令的足迹吗?”
此时月亮升起来了,清辉洒在菊瓣上,宛如覆了一层霜。子衡忽然想起什么,从袖中取出一个锦囊:“差点忘了,这是今早收到的,京城王兄寄来的,说是给你的重阳节礼物。”
煜明打开锦囊,里面是一支用菊枝雕成的笔,笔杆上刻着“晚节留香”四字。他握着笔,仿佛看见王兄在千里之外,对着菊花思念故人的模样。
“你看,”子衡指着菊圃中央的“凤凰振羽”,那花瓣如凤凰展翅,在月光下格外夺目,“即便相隔千里,这菊的情意却能相通。就像你我,还有王兄,虽然身处不同地方,却都守着一份如菊般的品格。”
煜明将菊笔收好,望着满园的菊花,忽然觉得,这云麓山的秋天,因为有了这些菊花,有了知己相伴,才显得如此丰盈。他想起诗中的“独守秋篱晚节彰”,忽然明白,所谓晚节,不仅是岁月的沉淀,更是对本心的坚守。
夜深了,两人坐在菊圃中的石桌旁,喝着菊花酒,聊着往事。月光下,菊花的影子在地上摇曳,如同舞者的裙摆。煜明看着子衡微醺的脸庞,忽然笑道:“明年秋天,我们要在菊圃里搭个茅亭,就叫‘陶然亭’,到时候请王兄来,我们一起在亭中赏菊、写诗、喝酒,如何?”
子衡闻言,眼中闪烁着光芒:“好!就这么定了!到时候我要亲自酿一坛‘醉流霞’,让王兄也尝尝我们云麓山的菊香。”
两人相视而笑,笑声惊起了草丛中的蟋蟀。远处的山峦在月光下若隐若现,而这东篱下的菊圃,却因着这份友情,在秋夜里绽放出最动人的光彩。或许,这就是最好的人生——在云麓山间,与知己为伴,种几株菊,写几首诗,守着一份如菊般傲然而温暖的情怀,直到岁月深处。
喜欢云麓词心录:白云着请大家收藏:()云麓词心录:白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