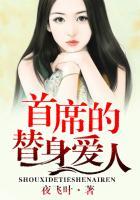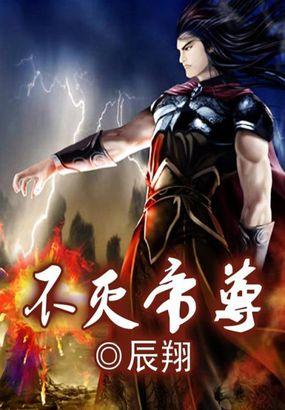笔趣阁>四合院局外人 > 第28章 承功的地方主政初体验(第1页)
第28章 承功的地方主政初体验(第1页)
1993年9月12日,渝州万盛区。放下前段日子调侃老七相亲的趣事,年轻的区长肖承功到任已近三个月。
回想6月18日,并非渝州直辖纪念日,却是他履新的日子。
市组织部的领导亲自将这位“能干的肖同志”送到万盛。肖承功身形挺拔,相貌堂堂,在普遍不算高大的渝州人中显得尤为突出。
渝州作为千年水陆码头,人口本就多元融合。他曾听身为军界泰斗的爷爷肖征提起,祖上或是宋时为抗蒙南迁的关中子弟。
任命大会上,肖承功端坐于调任九龙坡的前任王区长和组织部门领导身旁。
台下干部们的低声议论飘入他天生敏锐的耳中:“真年轻!”、“好高的个头!”、“听说是南岸南山肖将军的小孙子?”、“大科学家肖镇同志的儿子?”、“就是那位在沿海破过大案,又在京城…处理过棘手问题的?”、“对,背后有人称他‘肖阎王’、‘有毒镇公子’…不过肖家对家乡贡献是真大!”“唉,起点真高啊!”……显然,不少人最初将他视作又一位来基层“镀金”的京城子弟。
肖承功面上带着得体的微笑,与领导们轻声交谈,心中却已做好面对质疑的准备。
年龄是硬伤,但他的学历、过往政绩、群众口碑却是实打实的。
在陕甘宁蒙等西北省市,尤其在曾主政五年的口外镇,“肖镇长”是响当当的名号,群众基础极其深厚。
1987到1992年,他将一个人口仅万余、地处沙漠戈壁边缘的穷镇,打造成了全国百强镇前十的生态治理与工农发展典范。
当组织部门领导详细介绍肖承功的履历和口外镇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台下的窃窃私语渐渐变成了惊叹与佩服。
有能力的人在哪里都会闪光。以他的家世,本可在京城部委寻个舒适的岗位,即便下基层,也大可去富庶的沿海江南。但他选择了这里,选择了挑战。
初来乍到,肖承功谨记父亲教导: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是他早年跟随父亲处理全国性经济整顿工作时刻骨铭心的体会(其人大博士论文亦以此为重要课题)。
西北五年的沉淀,更铸就了他务实的作风和坚定的信念。相比在条件优越地区发展的表亲们,他深知自己选择的是一条更需磨砺的路。
接下来的两个月,他没有急于抛出任何宏伟蓝图,而是沉下身子,用脚步丈量万盛。
他走遍了辖内所有乡镇村落,考察了那些濒临破产、苦苦支撑的区属企业。
得益于“肖政堂教育基金会”自其亲爷爷肖政堂被追认为烈士后便持续投入,川东地区的基础教育普及程度远超全国平均水平,这为未来发展储备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然而,万盛的现实困境清晰而严峻:典型的喀斯特山区,石多土少,可耕稻田稀少,主要作物是玉米、土豆和红薯;曾为抗战和建国初期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铁矿等资源,到93年已近枯竭,剩余的多是贫矿,开采冶炼成本高昂,效益低下。
与拥有全国知名齿轮产业的邻区綦江相比,万盛的工业基础几乎一片空白。
虽然只要开口,他那在商界叱咤风云的兄长们(神龙国际、南山国际的掌舵人)随时可能支援项目或资金,但肖承功牢记父亲“绿色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叮嘱,决心绝不搞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
他要为万盛找到一条立足长远、契合实际的发展路径。
一个大胆的想法浮现:借助科技力量。他拨通了航天科工集团幺爸肖曙办公室的电话,提出合作请求——希望能利用遥感卫星资源,对万盛进行高精度地貌测绘,为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申请经过严格审批流程,并向渝州市委及当地驻军进行了完备的报备。
最终,肖承功按保密规定,派人从北京取回了经过处理的卫星测绘成果图。
当详尽的卫星地图铺满办公桌,肖承功仿佛着了魔。
他拿着放大镜,在办公室一趴就是一个星期,废寝忘食地研究每一道山脊、每一条沟壑、每一片可能的可利用区域。
区府大楼里甚至悄悄流传起“区长是不是太投入,有点‘走火入魔’?”的议论。
就在他全神贯注于地图之时,一则爆炸性新闻震动渝州乃至全国:由港城神龙国际投资集团旗下神龙基建与澳城南山国际投资集团旗下南山基建组成的“西部通道基建联合投资体”,与肃州、陕州、四川、贵州、粤西五省签署了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协议。
该联合体宣布,将采用国际通行的bot模式,垫资建设贯穿五省、连接西北内陆与南方出海口的国际标准高速公路网及重载电气化铁路网。
项目总投资规模高达1600亿人民币,由创业银行、复兴银行提供融资担保并发行专项债券(93A、b系列)。
更引人注目的是技术引进方案:首批机车及核心系统采用德国西门子技术,后续批次逐步由西门子与复兴神龙机车合资公司国产化(约定初期仅限国内市场)。
9月15日,国家计委等部委正式批准了这项名为“西部出海大通道”的战略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