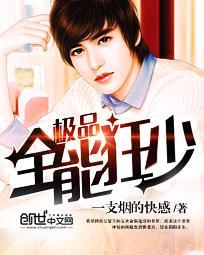笔趣阁>大明第一相 > 第164章 天问(第1页)
第164章 天问(第1页)
衙役前脚刚撤,几个榜奴便冲了过去,此时浆糊尚未粘牢,被两人各执一端揭了下来,用力一分扯成了两段。
他们也顾不得榜单长短,到手之后便胡乱一抓,塞进布囊系在颈下。
四周的人哪里受得了这个,自然是挤上去饱以老拳,到手的两人也不抵抗,抱着脑袋蜷着身子蹲在墙下,打死不退。
“果然……还是不行啊!
远处的张宜正惨然一笑,轻轻地叹息一声,眼睑不堪重负地垂了下来,遮住渐渐地失去了焦距的眼睛。
李步蟾有些木然,只觉得手上一沉,一颗雪白的脑袋无力地垂了下来,张宜正的脸上也没有痛苦,只有空洞,失去了希望的空洞。
“老祖!”
张子云从惊愕中回过神来,嘶声痛哭。
夏汉升与齐德隆面面相觑。
李步蟾中了第二,本来是挺好的事,可以乐呵一番,那边稳中的张宜正却没有上榜,失望之下撒手人寰。
他们与张子云交情不深,但也算朋友,碰到这样的事,也是唏嘘不已。
“子云兄,节哀顺变,张翁鲐背之寿,这是喜丧!”
张子云蹲在地上痛哭,李步蟾劝慰几句,起身对夏齐二人道,“大橘兄,东强兄,你们二位是本地土着,能否请你们帮着安排一下后事?”
那边张子云终于止住了戚容,走了过来,给三位友人长身揖拜,三人赶紧还礼。
“客套话就不说了!”
夏汉升摆摆手,正容道,“我现在回客栈,我那管家夏寿对红白事儿门清,我带他过来办事。”
“东强,那边那茶楼你熟,你去借块门板过来,若是没有门板,借两条春凳也行。”
“步蟾,你陪着子云,东强借到门板,你们就抬着张翁,去汪芝麻巷,我们在那里汇合!”
夏汉升指挥若定,他与齐德隆分头而去。
汪芝麻巷原本叫汪纸马巷,蒙元时一家姓汪的纸马店特别有名,后来长沙白事勾当大多到了那条小巷,后来因为纸马巷不好听,便改成了芝麻巷,取了个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彩头。
夏齐二人一去,张子云又蹲在张宜正的身旁,神情恍惚。
说到底他就是一个十五六岁的乡下少年,身处他乡,同时遭受秀才与老祖不翼而飞的双重暴击,换谁的脑子都是一片空白。
李步蟾从怀里掏出钱囊,从中取了一块碎银出来,里面还余了有二十多两。
这次出门,他的盘缠带得宽裕,考前的廪保、考后的报喜、拜师的礼品、取中的应酬,蒋桂枝都给他备齐了。
李步蟾蹲下来,搂着张子云的肩膀,抓过他的手,将钱囊塞到他的手里,“张翁寿尽天年,托体山阿,子云兄,这次我不能与你同行,回程之时再去官山祭拜。”
天气炎热,老人需要赶紧入土为安,今日收敛之后,张子云明日就将雇舟扶棺回乡,李步蟾既然取中秀才,过后还要参加簪花宴,还要办理一些事宜,没个三五天不能完事,肯定无法与张子云同行。
张子云木然接过钱囊,过了好一阵才反应过来,反手去抓李步蟾,“步蟾,这不合适……”
李步蟾压住他的手,“子云兄,朋友之间就不说这个了,日后有事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