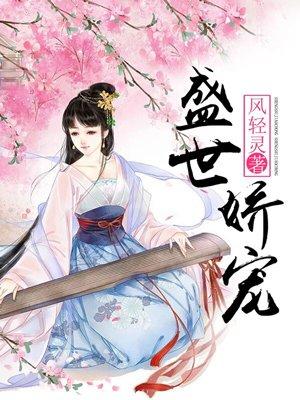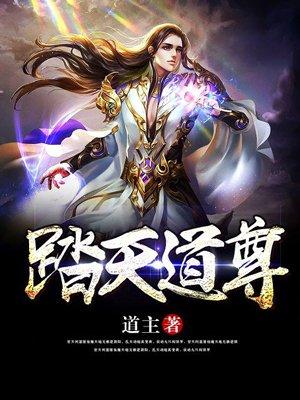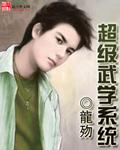笔趣阁>顶流影后竟被小糊咖拿捏了 > 第259章 公益项目再升级(第1页)
第259章 公益项目再升级(第1页)
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洒进屋内,照亮了桌上的笔记本和散落的照片。云倾月坐在窗边,手里拿着一张照片,眼神沉静而专注。时砚站在她身后,轻轻翻看着手机里的信息。
“基金会那边已经确认了资助计划。”他轻声说,“第一站的资金没问题。”
云倾月点头,将照片轻轻放在桌上。那是他们在贵州拍摄的一组影像中的一张——一个孩子蹲在破旧教室门口,用树枝在地上写字。阳光透过残缺的窗户照在他脸上,那双眼睛里透着对知识的渴望。
“我们要做的不只是记录。”她开口,“而是让这些故事被更多人看见,并且愿意为此做点什么。”
时砚走到她身边坐下,翻开他们整理好的资料。“我们之前关注过山区教育、留守儿童和环保问题,但这些都是独立的项目,缺乏系统性。”
“所以这次,我们要做一个长期计划。”云倾月目光坚定,“不是拍完就结束,而是持续跟进,形成真正的影响力。”
两人开始讨论具体的执行方案。他们查阅了多个公益项目的运作模式,分析各自的优缺点,也联系了几位曾参与类似项目的摄影师,了解实际操作中的难点与经验。
“有些项目只是一次性曝光,后续没有持续关注。”时砚皱眉,“孩子们的照片被人看到,然后呢?没人知道他们的生活有没有真的变好。”
“我们必须确保每一次拍摄都不仅仅是展示苦难,而是推动改变。”云倾月语气认真,“我们可以设立一个反馈机制,定期回访,记录变化,并向公众汇报进展。”
“还可以联合学校、公益组织,建立一个长效支持体系。”时砚补充道,“比如,我们在某地拍摄后,可以协助当地申请教育资源,或者促成志愿者支教行动。”
讨论逐渐深入,他们开始绘制详细的计划图。从选题、实地调研、拍摄、后期制作,到展览策划、媒体宣传、社会联动,每一个环节都被仔细考量。
“我们得先确定几个重点区域。”云倾月拿出地图,在中国西南部圈出几处偏远地区,“这里是云南怒江大峡谷,交通闭塞,教育资源匮乏;这里是川西高原,冬季漫长,很多孩子上学要走十几公里山路;还有这里,广西喀斯特地貌区,水资源短缺,影响农业发展。”
时砚一边听一边记下要点,“我们可以分阶段推进,先从最容易进入的区域开始,积累经验和资源后,再拓展到更复杂的地区。”
他们还计划邀请一些志同道合的摄影爱好者加入,组成一支小型团队,既能提高效率,也能让更多人参与到这项事业中来。
“如果能带动更多年轻人关注这些问题,那就更有意义了。”时砚笑着说。
云倾月看了他一眼,眼中闪过一丝温柔,“你还是像以前一样,眼里有光。”
“因为这次是我真正想做的事。”他回答得很认真。
接下来几天,他们不断调整和完善方案,同时联系相关机构,争取更多的合作机会。基金会的支持让他们有了初步的资金保障,而一些公益组织的响应也让他们的计划更具可行性。
“有个组织愿意帮我们对接云南那边的学校。”时砚兴奋地说,“他们已经在当地做了几年助学项目,有现成的联系方式。”
“太好了。”云倾月立刻打开电脑,调出之前的调研资料,“我们可以提前做一些功课,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更具体的拍摄方向。”
随着计划的逐步成型,他们也开始着手准备设备和物资。虽然已经有过多次实地拍摄的经验,但这次不同以往,他们需要长时间驻扎,面对更复杂的生活环境。
“帐篷、便携式电源、净水器、药品……”时砚一边列清单一边念叨,“还有保暖衣物,云南早晚温差大。”
云倾月则负责联络摄影师朋友,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同行。“我们不求专业水平,只要真心想做这件事的人。”
就在他们忙碌筹备的同时,一封来自评审团的邮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是L。发来的。”时砚点开邮件,快速浏览内容,“他说行业内部已经开始整顿,幕后操作者已经被彻底封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