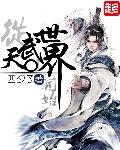笔趣阁>英烈传奇 > 第208章 群英毕至聚汴州新幕初开待风起(第1页)
第208章 群英毕至聚汴州新幕初开待风起(第1页)
大唐开武二十六年深秋,汴州的空气里已带着明显的凉意,运河水面上甚至泛起了薄薄的晨雾。龙天策微服私访三日,对汴州的盘根错节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世家势力比睢阳更深,官场习气比睢阳更重,推行新政的阻力,远超预期。
这日傍晚,他回到临时下榻的驿馆,屏退左右,只留下玉倾城和夜凌。驿馆的烛火摇曳,映着他沉思的脸庞。
“汴州不比睢阳。”龙天策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凝重,“这里的水太深,单靠我们几个人,怕是难以撼动。”
玉倾城递过一杯热茶:“你想调人?”
“嗯。”龙天策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决断,“新政要在河南道铺开,必须有自己的班底。那些盘根错节的本地官员靠不住,我们需要绝对可靠、能打硬仗的人。”
夜凌抱拳道:“大人想调谁?属下即刻去办。”
“不急,需得请旨。”龙天策走到案前,铺开宣纸,提笔蘸墨,“我要调的人,不少都在幽州任职,没有陛下的旨意,动不了。”
他沉吟片刻,笔尖在纸上落下一个个名字,每写一个,都停顿片刻,仿佛在回忆那人的模样与能耐。
“文有三杰:邓铿、房衍、杜哲。”
邓铿,曾是他在幽州时的长史,沉稳干练,最擅处理繁杂政务,尤其擅长调和各方矛盾,当年幽州各族能和睦相处,邓铿功不可没。
房衍,谋士出身,心思缜密,善于谋划长远,往往能在看似无解的困局中,找到破局的关键,是龙天策在淮南平叛时的“智囊”。
杜哲,精通钱粮、漕运,曾在幽州主持军需,将混乱的军饷打理得井井有条,算账之精,堪比账房先生,却又有全局视野。
“武有七将:风影、鲁大胜、鲁元达、云澈、黄强、林冲、吴天狼。”
风影,人如其名,来去如风,擅长侦查、渗透,麾下有一支“影子”小队,能在无声无息中获取情报,是龙天策最锋利的“暗刃”。
鲁大胜、鲁元达兄弟,是军中有名的猛将,鲁大胜力能扛鼎,使一对重锤;鲁元达看似粗犷,却擅长防御,人称“铁壁”,兄弟俩配合默契,是攻坚拔寨的好手。
云澈,箭术通神,能百步穿杨,更擅长训练弓箭手,当年幽州军的神射手营,便是他一手打造。
黄强,出身农家,熟悉各种地形,尤其擅长山地作战,性格坚韧,越是艰险越向前。
林冲,善使长槊,枪法(槊法)精湛,曾是禁军教头,因得罪权贵被贬幽州,得龙天策赏识重用,为人沉稳,治军极严。
吴天狼,生有一双异瞳,一白一黑,透着一股野性,使一柄九环大金刀,勇猛无匹,打起仗来悍不畏死,是冲锋陷阵的先锋猛将,但平日里却极重义气。
“再加上我们身边的……”龙天策的笔尖顿在纸上,笑意渐浓,“夜凌,你自不必说;刘晔先生深谋远虑,是坐镇中枢的良才;花蓉心思细腻,擅长情报分析与人心洞察;赵胜熟悉商路民生,能通有无、聚财货。”
他将笔一搁,看着纸上密密麻麻的名字,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有这些人在,何愁新政不成?何愁河南道不平?”
玉倾城看着名单,亦点头道:“这些人,或是与你共过生死,或是经你亲手提拔,忠诚可靠,各有所长,确实是推行新政的最佳人选。”
“好!”龙天策拿起写好的名单,“夜凌,即刻将这份奏折送往神都,务必亲手交到陛下手中。”
“是!”夜凌接过奏折,转身消失在夜色中。
三日后,神都紫宸殿。
秦正阳看着龙天策的奏折,越看眉头越舒展,最后竟抚掌大笑:“好一个龙天策!调兵遣将,竟把主意打到幽州去了!不过……他这眼光,确实独到!”
奏折上,龙天策不仅列出了拟调人员名单,还详细说明了每个人的特长、功绩,以及在河南道新政中能发挥的作用,字里行间,透着对这些人的信任与倚重,也透着他推行新政的决心。
“陛下,”杨皇后凑过来看了名单,笑道,“这些人,皆是龙天策的心腹旧部,能力出众,他调他们来河南道,显然是要大展拳脚了。”
“是啊。”秦正阳点头,眼中闪过一丝欣慰,“汴州乃中原重镇,河南道是大唐的粮仓,非有得力人手,难以推行新政。龙天策此举,是深思熟虑后的决断。”
他想起邓铿的沉稳,房衍的智谋,想起风影的迅捷,吴天狼的勇猛……这些人,他也略有耳闻,确实都是难得的人才。
“只是,”杨皇后轻声道,“将幽州的得力干将调走,会不会影响幽州的防务?毕竟契丹、奚族虽暂时安分,却也不能掉以轻心。”
“无妨。”秦正阳摆手,“幽州如今根基稳固,留下的将领足以镇守。再说,河南道的稳定,关乎大唐的气运,比幽州的一时防务更重要。龙天策要做大事,朕岂能不支持?”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