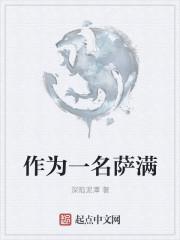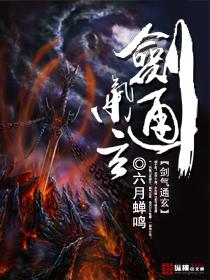笔趣阁>中国野史大甩卖 > 第11章 李清照状告后夫(第1页)
第11章 李清照状告后夫(第1页)
靖康二年(1127年)的那场浩劫,使无数人的命运坠入深渊,其中便有名满天下的女词人——李清照。当时她刚过不惑之年,本与丈夫赵明诚在青州“归来堂”里赌书泼茶,沉浸于金石书画的世界,却不想金人铁蹄踏破汴京,徽钦二帝被俘,史称“靖康之变”。
赵明诚时任江宁知府,后因失职罢官,夫妻二人携着毕生收藏的古籍金石南下避难。谁曾想,建炎三年(1129年),赵明诚在前往湖州赴任途中染病,竟在南京(今河南商丘)撒手人寰。这一死,不仅让李清照失去了相伴二十八年的知己,更让她成了乱世中无依无靠的孤孀。
李清照守着丈夫的灵柩,又望着堆积如山的金石文物,心中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彼时江南已是宋室偏安之地,高宗赵构在临安(今杭州)登基,可金兵南下追击,战火未歇。李清照一介女流,带着沉重的藏品辗转于越州、衢州、温州等地,其间不少珍本古器或被乱兵所掠,或因颠沛遗失,昔日“赌书消得泼茶香”的雅致,早已化作“风住尘香花已尽”的悲凉。
到了绍兴二年(1132年),李清照总算在杭州暂时安定下来。此时她年近五十,孑然一身,生活困顿。古代女子无独立经济来源,尤其像她这样曾是官宦夫人、如今家道中落的寡妇,处境更是艰难。左邻右舍看她的眼神,多半是同情里掺着好奇,背后少不了嚼舌根:“瞧这李夫人,以前多风光,如今连个依靠都没有。”
就在这时候,一个名叫张汝舟的男人走进了她的生活。这张汝舟,字仲弼,当时在江南某州县做个小官,自称是赵明诚的故交,听闻李清照的遭遇后,便时常来嘘寒问暖,送些柴米油盐。他生得一副好皮囊,说起话来更是甜如蜜糖,“夫人这般才貌,岂能久居困顿?某虽不才,愿为夫人遮风挡雨”之类的话,说得李清照心中泛起涟漪。
大家可能要问:李清照何等聪慧,岂会轻易相信一个陌生男人?这里头可有不少原因:一来,她当时确实孤苦无依,连整理丈夫遗着《金石录》都力不从心,急需一个帮手;二来,张汝舟极善伪装,他先是拿出几封“早年与赵明诚的书信”,又对金石之学侃侃而谈,让李清照误以为遇到了可以托付之人;三来,宋代社会对寡妇再嫁虽有非议,却也并非完全禁止,尤其像李清照这样没有子女的寡妇,再嫁在法理上是允许的。
于是,在张汝舟持续数月的“温情攻势”下,李清照那颗历经沧桑的心,竟也生出了一丝希冀。她想:或许,晚年能有个知冷知热的伴,也算不负这残生。却不知,这一决定,竟让她卷入了一场远比乱世更险恶的风波。
绍兴二年(1132年)暮春,杭州西子湖畔的柳絮飘飞如雪。李清照在张汝舟的操办下,低调地举行了再嫁仪式。没有锣鼓喧天,没有亲友满堂,只有几张简单的桌案,几样家常酒菜。李清照穿着一身半旧的素色罗裙,看着眼前忙前忙后的张汝舟,心中五味杂陈。她举杯轻抿,脑海里却闪过与赵明诚在“归来堂”中,以胜负决定饮茶先后,常常笑到茶泼满身的场景。
婚后最初的日子,张汝舟确实表现得体贴入微。他会亲自下厨做几样李清照爱吃的小菜,会陪着她在庭院里散步,听她吟诵新词。李清照也渐渐放下心防,甚至将自己收藏的部分金石拓片拿出来与他欣赏。然而,没过多久,张汝舟的真面目便露了馅出来。
原来,这张汝舟娶李清照,根本不是看中她的才情,而是觊觎她手中的金石文物。赵明诚毕生搜集的商周彝器、汉唐碑刻,那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张汝舟原以为娶了李清照,这些东西便尽入囊中,谁知他翻箱倒柜,却发现大部分珍品在南渡途中已遗失,剩下的不过是些普通拓片和残缺古籍。
这天晚上,张汝舟喝了几杯闷酒,见李清照在灯下整理书卷,便没好气道:“整天摆弄这些破纸片子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我看你根本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当初还装得那么神秘!”
李清照闻言一惊,抬头看着眼前这个陌生的男人,他脸上的温情早已被贪婪和不耐取代。她强压怒火道:“这些都是先夫心血所系,岂可用钱财衡量?”
“先夫先夫,你心里只有那个死鬼!”张汝舟猛地一拍桌子,“我告诉你李清照,你如今是我张汝舟的妻子,就得听我的!那些破玩意儿赶紧卖了换钱,不然有你好果子吃!”
这一下,如同被冰水浇头,让李清照彻底清醒。她这才明白,自己错看了人,这张汝舟分明是个利欲熏心的小人!接下来的日子,张汝舟的态度越发恶劣。他见软的不行,便来硬的,先是言语辱骂,后来竟发展到动手推搡打骂。有一次,李清照不肯将一幅王羲之的摹本交给他,张汝舟竟一把抢过书卷撕得粉碎,还指着她的鼻子骂:“你这老妇,不识抬举!若不是看你有点虚名,谁愿娶你?”
李清照蜷缩在角落,看着满地狼藉的残卷,泪水无声滑落。她想起赵明诚在世时,两人对文物视若珍宝,连翻阅都要先净手焚香,何曾受过这等屈辱?此时她才幡然醒悟:张汝舟当初的“温情”,不过是精心编织的骗局;那所谓的“故交”,恐怕也是子虚乌有。
更让她心寒的是,张汝舟不仅贪财,还品行不端。李清照偶然发现,他的官印文书似乎有伪造痕迹,追问之下,张汝舟支支吾吾,竟露出了马脚。原来,他的官职是通过虚报举数(宋代科举中举需有人推荐,虚报推荐次数是欺君之罪)得来的,平日里还克扣军饷,中饱私囊。这一下,李清照心中最后一丝幻想也破灭了——这哪里是良人,分明是个伪君子!
李清照萌生啦离婚都想法,然而在宋代,女子要离婚,难如登天。当时的法律规定,“妻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除非丈夫有“七出”之罪(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或丈夫失踪三年以上,妻子才能提出离婚。而张汝舟虽然家暴、贪财,但并未犯“七出”中的条款,更何况他是官吏,社会地位比李清照高(尽管是个小官)。
换作一般女子,或许只能忍气吞声,在不幸的婚姻里耗尽余生。但李清照是谁?她是能写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奇女子,是骨子里透着刚烈的易安居士!她岂能容忍自己与这样一个卑劣之徒共度余生?
经过几夜无眠的思索,李清照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不仅要离婚,还要告张汝舟欺君罔上之罪!这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之举——妻子告丈夫,本就违背“夫为妻纲”的伦理,更何况告的是欺君之罪,一旦告成,张汝舟虽必死无疑,而她自己,按照宋代法律,“妻告夫,虽属实,仍需徒刑二年”。
也就是说,李清照若要离婚,必须先把自己送进大牢。
身边的亲友得知此事,无不大惊失色,纷纷来劝:“夫人三思啊!告夫乃是大逆不道,何况还要坐牢,值吗?”
李清照却异常坚决,她缓缓道:“我宁可坐牢,也不愿与这等败类同床共枕。身狱易脱,心狱难离。若为自由故,二年徒刑又何妨?”她的眼神里,没有恐惧,没有哀伤只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绍兴二年(1132年)九月,李清照一纸诉状递到了临安府衙,状告丈夫张汝舟“妄增举数”“贪污军饷”。知府大人接过诉状,一看原告是李清照,被告是她的丈夫,顿时皱紧了眉头。这案子太棘手了,一边是名满天下的才女,一边是朝廷命官,无论怎么判,都可能引来非议。
张汝舟得知李清照竟敢告他,气得暴跳如雷:“好你个李清照!你竟敢告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你以为官府会帮你这妇道人家?我告诉你,不出三日,我就让你尝尝牢饭的滋味!”
李清照冷冷地看着他,道:“你贪赃枉法,欺君罔上,本就该受国法惩处。我告你,是替天行道,也求自己能够解脱。”
很快,临安府开堂审理此案。公堂上,李清照一身素衣,从容不迫地陈述张汝舟虚报举数的证据,并找到了当年知情的同僚作证。张汝舟起初还百般抵赖,可在确凿证据面前,终于无法自圆其说,被打得皮开肉绽(宋代审案常用刑讯),只得招认。
按律,张汝舟“妄增举数”,当处流放之刑(宋代对欺君之罪处罚较重,但视情节可免死);而李清照“妻告夫”,虽属实,仍需判徒刑二年。消息传出,杭州城为之哗然。人们既震惊于李清照的刚烈,又为她即将面临的牢狱之灾感到惋惜。
就在李清照即将入狱之际,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当时的翰林学士綦(qi)崇礼。这綦崇礼与赵明诚有些交情,也曾受过李清照父亲李格非(苏门后四学士之一)的恩惠,对李清照的才学和遭遇十分同情。更重要的是,他为人正直,看不惯张汝舟的卑劣行径。
綦崇礼得知李清照的案子后,立刻意识到其中的不公。他想:李清照告夫虽是事实,但张汝舟本就是罪有应得,岂能让才女因仗义执言而身陷囹圄?于是,他连夜起草奏章,向高宗皇帝进言,陈明李清照再嫁的无奈、张汝舟的险恶用心,以及李清照告夫实乃“不得已而为之”,请求皇帝法外开恩,赦免李清照的徒刑。
綦崇礼在奏章中写道:“清照不终晚节,卷进家讼,甚为可惜。然张汝舟欺君贪墨,罪有应得。清照告夫,虽违伦理,实乃为民除害,为己脱厄。伏望陛下怜其才、悯其遇,赦其刑罚,使才女得免牢狱之苦。”
高宗皇帝此时正忙于稳固南宋政权,对这种家务事本不想多管,但架不住綦崇礼等大臣的再三进谏,又念及李清照的才名,最终下了一道谕旨:“李清照告夫属实,然其情可悯,着免其徒刑,准其与张汝舟离异。张汝舟欺君贪墨,革去官职,流放柳州。”
这道谕旨一下,李清照总算逃过了牢狱之灾。拿到离婚判决书的那天,杭州下着蒙蒙细雨。李清照站在窗前,看着雨丝打湿庭院里的芭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口气,她憋了太久,从再嫁的悔恨,到婚变的痛苦,再到告状的决绝,如今终于得以舒展。
张汝舟被削职流放,从此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而李清照,虽然摆脱了不幸的婚姻,却也因这场风波受尽了世人的非议。有人骂她“晚节不保”,有人笑她“识人不明”,连一些昔日的朋友也对她避之不及。
面对这些流言蜚语,李清照没有辩解。她知道,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一个女子竟敢主动休夫、告夫,本就是对礼教的挑战,必然要承受世俗的压力。她只是将所有的悲愤与感慨,都写进了词里: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zéměng)舟,载不动许多愁。”
这首《武陵春》,道尽了她当时的心境——国破家亡之痛,夫死再嫁之悔,婚变离异之辱,种种愁绪,竟连小小的船儿都载不动。
这场风波过后,李清照彻底断了再嫁的念头,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和整理丈夫遗着中。她在杭州、绍兴等地辗转流离,虽然生活依旧清贫,但心境却愈发豁达。她写下“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借古讽今,表达对南宋朝廷偏安一隅的不满;她写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将个人的悲苦升华为乱世中无数流民的共同哀愁。
她的词风也因这场变故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前期多写闺阁闲情、夫妻恩爱,如“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沾衣透”;后期则多写国破家亡、身世飘零,如“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这种从婉约到沉郁的转变,不仅是个人命运的折射,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到了晚年,李清照终于在临安定居下来,靠着替人抄书、卖字画维持生计。她将赵明诚的《金石录》整理完成,并作《金石录后序》,详细记述了夫妻二人搜集金石的艰辛与乐趣,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亡夫的思念和对过往岁月的追忆。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这位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女词人,在临安悄然离世,享年七十一岁。她的一生,经历了北宋的繁华,南宋的动荡,有过琴瑟和鸣的幸福,也有过再嫁婚变的屈辱,但无论顺境逆境,她始终保持着独立的人格和对精神自由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