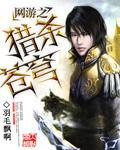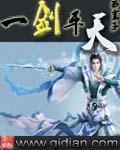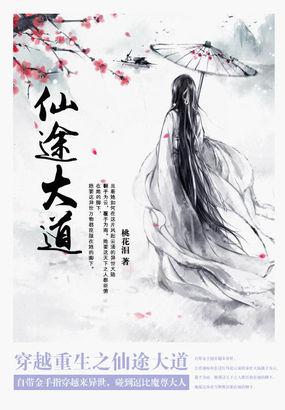笔趣阁>天幕直播靖难,朱棣你别跑! > 第225章 败家子背后的孙太后(第1页)
第225章 败家子背后的孙太后(第1页)
《明史·卷一百三十》的记载被天幕清晰地拓印在虚空:
【石亨等谋夺门,先密白太后,许之。朱祈镇复辟,上徽号曰圣烈慈寿皇太后。】
短短两行字,却像投入滚油的火星,瞬间点燃了朱元璋压抑的怒火!
“密白太后?许之?!”朱元璋猛地一拍龙椅扶手,紫檀木出沉闷的痛鸣。
他霍然站起,须戟张,那双洞察世事的鹰目此刻寒光四射,死死钉在“太后”二字上,仿佛要将那两个字灼穿!“后宫干政?!谁给她的胆子!祖宗家法何在?!朕的《皇明祖训》是摆设吗?!”
咆哮声如同惊雷,震得殿梁嗡嗡作响。朱元璋最痛恨、最严防死守的,就是除了马皇后之外的后宫妇人染指权柄!这“许之”二字,无异于触碰了他的绝对逆鳞!哪怕这个“太后”是他未曾谋面的曾孙媳妇,也绝不容忍!
太子朱标心头一凛,连忙劝道:“父皇息怒!天幕所述乃后世之事,或有隐情……”他虽也震惊于太后竟参与政变,但更担心父皇盛怒伤身。
蓝玉抱着胳膊,嘴角勾起毫不掩饰的讥诮,声音不大却清晰地传入众人耳中:“呵,好一个‘圣烈慈寿’!这徽号听着响亮,却是靠儿子政变抢回来的?这位孙太后,手腕了得啊。”这话如同火上浇油,让朱元璋的脸色更加难看。
耿炳文也捋着胡子,瓮声瓮气地补刀:“难怪那朱祁镇小子如此……啧,看来根儿上就歪了!”他虽未明说,但“土木堡败家子”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
仿佛为了回应洪武君臣的震怒与疑惑,天幕的画面倏然流转,时光倒退回数十年前的永乐盛世。
场景是庄严而喜庆的皇宫。永乐十五年,为皇太孙朱瞻基选妃的盛事正在进行。年迈却威严犹存的永乐大帝朱棣端坐御座,下方,主持选妃的太子妃张氏(未来的张太后)正恭敬地汇报着最终筛选出的两位贵女:光禄寺卿胡荣之女胡善祥,永城主簿孙忠之女孙氏。
“司天监观天象,言‘后星直鲁也’。”天幕的画外音平静叙述,“帝询司天监,得此结论,意即未来皇后当属山东籍贯。胡、孙二女祖籍皆为山东,然孙氏自幼长于河南……”
画面中,朱棣威严的目光扫过两位少女的画像与资料,最终定格在胡善祥那份上。“立胡氏为皇太孙妃,孙氏为嫔。”圣意已决。
奉天殿内,马皇后一直凝神细听,当听到“司天监言后星在鲁”时,她秀美端庄的眉头便微微蹙起。此刻看着天幕上两位少女的对比——胡氏画像端庄持重,孙氏则眉眼间天然带着一股灵动娇媚——马皇后轻轻叹了口气,声音带着洞察世事的了然与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这司天监之言,怕是……未必全为天意吧?那孙氏女,观其形容气质,怕是个心思活络、善邀君心的。”她顿了顿,用了一个极其精准却带着贬义的词,“狐媚的。”
徐达闻言,目光也凝重起来。他虽为武将,但也深知后宫风气对朝堂的影响。张太后选妃时,胡氏显然更符合“母仪天下”的端庄标准,这孙氏能入选并最终掀起如此波澜,其手段心性,恐怕正如马皇后所料,非同一般。
朱元璋冷哼一声,虽未言语,但眼中的厉色更盛。他想起自己亲自为朱高炽选的张氏(未来的张太后),那才是真正贤德的模样!这孙氏,看着就不是安分的主!
天幕画面快流转,将孙氏如何在朱瞻基心中一步步取代胡氏的历程清晰展现。
成为皇太孙嫔的孙氏,“幼有美色”(天幕特意强调),且“善承上意”,处处投朱瞻基所好,让他“甚有成就感”。而正妃胡氏则“举止庄重,无媚顺之态”,甚至“每乘间规讽”,经常劝谏丈夫,让年轻的朱瞻基感到“不自在”。
朱棣看着天幕上自己的好圣孙朱瞻基对胡氏的疏远和对孙氏的沉迷,脸色铁青。他仿佛看到了一个被美色迷昏了头的蠢货!身负江山社稷之重,竟如此不知轻重!
画面转至宣德朝。朱瞻基登基为帝,胡氏为后,孙氏为贵妃。但朱瞻基对孙氏的宠爱已到了公然逾制的地步——破例赐予本应皇后独享的金印!天幕特写那方象征着无上恩宠和逾越礼法的金印,金光刺眼。
“胡闹!”朱元璋怒斥,“祖宗规制何在?!贵妃赐金印?他朱瞻基眼里还有没有王法!”这简直是为日后废后埋下的伏笔!
果然,宣德二年,孙贵妃诞下朱祁镇。天幕清晰地展现朱瞻基如何欣喜若狂,如何为保孙氏“龙胎”免去其向太后、皇后问安的礼数(这是极大的特权与不敬),如何迫不及待地在儿子出生仅两个月后,便召集阁臣,提出废胡立孙!
阁臣杨士奇等人初时激烈反对:“胡后无过!”“无废后先例!”“嫡庶纲常不可乱!”但画面中朱瞻基脸色阴沉,明显不悦。随后,杨荣等人私下劝杨士奇:“皇上意已决,徒争无益。”最终,在朱瞻基的逼迫下,胡皇后“称病”上表辞位,退居冷宫,孙氏登上后位。
“无耻之尤!”蓝玉嗤笑出声,“什么‘母以子贵’?分明是宠妾灭妻!这朱瞻基,为了个女人,脸都不要了!”耿炳文也连连摇头:“昏聩!如此行事,岂能服众?难怪日后生出祸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