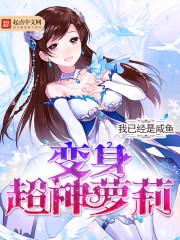笔趣阁>天幕直播靖难,朱棣你别跑! > 第225章 败家子背后的孙太后(第2页)
第225章 败家子背后的孙太后(第2页)
朱元璋看着天幕上孙氏如愿以偿戴上凤冠,而贤德的胡后被废黜幽居,气得胸口剧烈起伏。他指着天幕,手指都在颤抖:“看到了吗?标儿!老四!你们都看到了吗?!祸根!这就是祸根!为了个狐媚妇人,坏了嫡庶纲常,乱了朝堂法度!这孙氏,就是那败家子朱祁镇的亲娘!上梁不正下梁歪!”
朱棣脸色煞白,看着自己孙子(朱瞻基)的昏聩行为,听着父皇的怒斥,只觉得无地自容,一股冰冷的寒意从心底升起。
天幕画面急转,来到正统十四年。土木堡噩耗传来,天子被俘,二十万精锐尽丧,京城危如累卵。
画面聚焦深宫。孙太后(此时已因儿子登基为帝而成为皇太后)惊闻噩耗,第一反应并非社稷安危,而是——皇位继承!
“太后诏立皇长子见深为皇太子,时年二岁,命郕王辅之。”天幕文字冰冷地揭示她的私心:抢在郕王朱祁钰(朱祁镇庶弟,当时监国)坐稳监国位置前,火立自己年仅两岁的孙子朱见深为太子,企图用“太子”之名将皇位继承权牢牢锁死在朱祁镇一脉!让朱祁钰只能做辅佐幼主的“临时工”。
“混账!”朱元璋气得须皆张,“国难当头!强敌压境!不思如何御敌保国,先忙着给自己孙子抢位置?!这妇人何其自私!何其短视!”他简直无法理解,江山都要倾覆了,她脑子里还只装着那点私利?
接着,画面显示孙太后为赎回儿子朱祁镇,几乎掏空了后宫积蓄,派八匹快马运送财宝给瓦剌。“慈母之心?”天幕画外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讽刺。
而当瓦剌挟持朱祁镇兵临北京城下,兵部侍郎于谦等人为绝瓦剌要挟之念、凝聚抗敌力量,提出拥立郕王朱祁钰为帝,尊朱祁镇为太上皇的万全之策时,画面却给了孙太后一个长长的特写——犹豫!挣扎!
“八月二十三日上奏……八月二十九日方许。”天幕点出这关键的六天犹豫期。“若非亡国在即,孙太后恐难舍其子之帝位。”
“六天!整整六天!”朱标痛心疾,“这六天,前线将士在浴血,京城百姓在恐慌!她身为太后,竟为一己私心,置江山社稷于不顾!这犹豫的每一刻,都是在拿大明的国运下注啊!”他终于深刻理解了父皇为何如此痛恨后宫干政,这孙太后的每一个决策,都带着致命的私心!
徐达也沉痛摇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此妇人之仁,几误国本!”若非于谦等人力挽狂澜,后果不堪设想。
天幕画面最后定格在景泰八年。病重的景泰帝朱祁钰膝下无子(其独子朱见济已夭折),皇位继承悬而未决。
石亨、徐有贞等投机者,为抢“拥立之功”,秘密联络孙太后,策划“夺门之变”。画面中,深宫内的孙太后听闻要让儿子朱祁镇复辟,眼中瞬间爆出惊人的亮光,毫不犹豫地在密旨上用了印!
“许之!”天幕再次响起这两个字,与开篇呼应。这一次,朱元璋没有再咆哮,只是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眼中是彻底的心寒与失望。这孙氏,为了儿子复位,为了娘家长兄孙继宗得封侯爵(会昌侯),竟不惜勾结外臣,动政变!将刚刚从土木堡惨败中恢复些许元气的大明朝,再次拖入血腥的权力倾轧!
画面结束,一行总结性的金色大字浮现:
【铁打的太后,流水的皇帝。孙氏历经三朝,权欲私心,终成明室巨祸之引。】
紧接着,明末大儒顾炎武的警句轰然呈现:
【王道之大,始于闺门!】
奉天殿内,死一般的寂静。
朱元璋缓缓坐回龙椅,疲惫地闭上眼,良久,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冰冷彻骨的话,如同为这个“厉害”的孙太后一生下了定论:
“家门不正,祸及国门!这败家子朱祁镇的背后……站着一个更败家的娘!”他猛地睁开眼,目光如刀锋般扫过阶下所有皇子,尤其是朱棣和朱标,声音斩钉截铁,带着不容置疑的警告:
“都给咱听好了!选妃立后,重贤德!若再有此等狐媚祸国之辈入我朱家之门,乱我大明纲常……朕,绝不姑息!定斩不饶!”
那凛冽的杀意,让整个奉天殿的温度都骤然下降。天幕的光芒渐渐暗去,留下洪武君臣心头一片沉重的阴霾,以及对“闺门之教”前所未有的警醒。